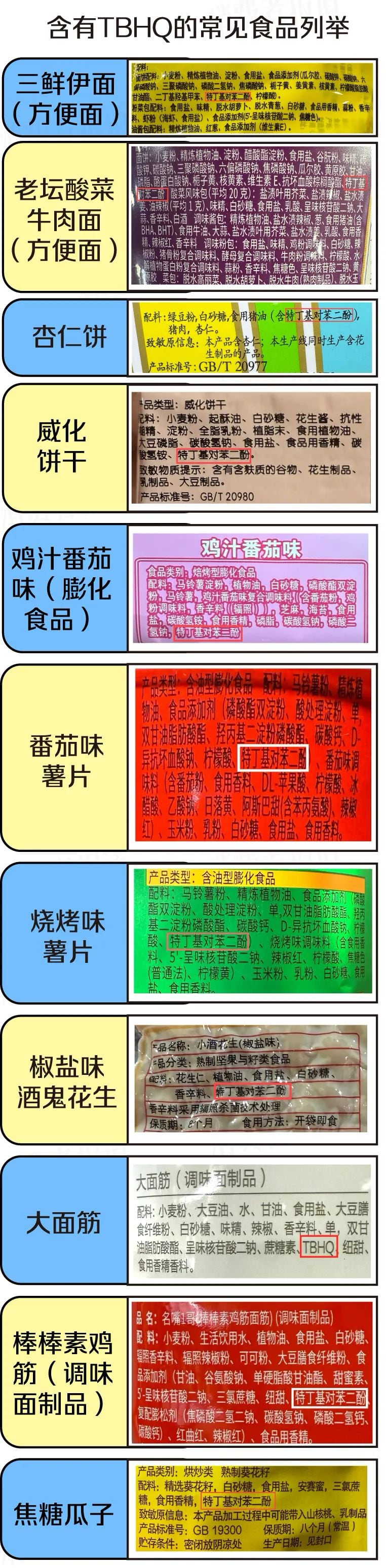人類發現了米食之后,就學會炒飯了。炒飯應該是最遍及的一道菜,但不入名點之流,最不被人看重,其實是最根本最好吃的東西。

題圖:圖蟲·創意
——蔡瀾
來源:食味藝文志
作者:魏水華
炒飯,也許是“揚州”這座城市,最廣而告之的招牌。
和安徽牛肉板面、重慶雞公煲、蘭州拉面、澳門豆撈這些“假戶口”美食不同,在揚州,的確能找到各種各樣的揚州炒飯。
但奇異的是,假如要正兒八經吃一頓揚州早茶、或許一頓淮揚菜,炒飯真的不多見。
這一桌子是趣園的。

△圖片來源:魏水華攝
這一桌子是冶春茶社的。

△圖片來源:魏水華攝
這一桌子是富春茶社的。

△圖片來源:魏水華攝
這一桌子是共和春的。

△圖片來源:魏水華攝
蒸點、湯點、小菜、葷物完全,但在各類揚州美食薈萃的局面上,就是沒有炒飯。
終究是什么,形成了炒飯在揚州餐桌上的游離?

揚州炒飯從何而來
炒飯究竟是不是揚州的傳統美食?
雖然很多人對這個成績有質疑,但中國現代的炒飯,的確與揚州地域有著深入的關系。
中國最早的關于炒飯的記載,來自隋煬帝的御廚謝諷,他的著作《食經》里,記載了一種“碎金飯”,所謂“碎金”,描繪的就是炒碎混入米飯中粒粒如金的雞蛋。
揚州是隋煬帝駐留工夫最多的城市。滅南陳時,他是三軍總帥;當太子之前,他是揚州總管;再后來的開鑿大運河、坐龍舟、賞瓊花、品螃蟹,隋煬帝生平的每一件事,都深入地打上了揚州的印記。
當然,也包羅江南大廚制造的炒飯。游曾經成為經濟興旺、人口稀疏、教育水平很高的國度稅收重地。對外地人來說,食用油不再是高攀不起的貴族專享,而是小康之家改善生活都能用度的食材。
再加上灌鋼法的推行,讓鋼鐵冶煉的質量進步、本錢進一步降低,除了培養“明光鎧”與“唐陌刀”等等在中國冷兵器史上大名鼎鼎的武備外,還讓圓底、薄邊、導熱速度快、翻動效率高的鐵質炒鍋在官方開端普及。

△圖片來源:pixabay
現實上,隨著三國、兩晉和南朝長達三個世紀的北方大開發,長江中下
從此當前,煎、烤、煮、蒸在西餐譜系上退居二線,技術含量更高、烹飪器皿要求更復雜的炒占據相對霸主位置。
尤其是米飯這種淀粉含量極高的食品,易糊易焦,在沒有適宜炊具的時代,只能以蒸煮漸漸料理。但在中式炒鍋降生和普及之后,熱油猛炒、疾速翻動、焦香到位、鑊氣逼人的炒飯,才有了技術上的根底。
炒飯降生在公元六世紀的,富庶揚州地域,是可信的。
中國飲食史的風趣之處在于,當一切客不雅條件有利于某種食物成熟開展的時分,也許也就意味著這種食物加入審美體系的時分。
在隋唐之后千余年的歷史中,炒飯并未更多地呈現在文獻里。比方記載了300多種南北飯肴的《隨園食單》,竟然對炒飯只字未提。
袁枚所處的清中葉,絕不成能沒有炒飯。但《隨園》不收錄炒飯的做法,卻表露了作者關于炒飯這種食物幽微的心思。
不下臺面。
這種狀況,與炒飯的普及和本錢降低有關。宋當前,隨著煤炭開采技術的成熟,呈現了社會面的大規模制瓷、冶鐵。依據美國學者郝若貝的計算,在冶鐵業最為興盛的宋神宗在位時期,鋼鐵年產量在七萬五千噸至十五萬噸,全球第一。
這讓本來只能使用于軍事和貴族生活的鐵器真正走進了平民百姓家。壓榨植物油、烹制炒飯最困難的門檻成了不費吹灰之力的環節。
物以稀為貴,不稀罕了,也就不值得推崇了。
更重要的是,隨著唐宋以來科舉制度的定型、門閥的衰落、程朱理學的普及推行,文人士大夫開端成為中國社會辦理階級的中心。隨之而盛行的,是崇尚油膩、中庸、精密、俗氣的文人審美。
代表西餐最頂尖味道的螃蟹、刀魚、鰣魚抽象就此養成;科舉考試人才比例冠絕全國的江浙平原降生了有 “文人菜”佳譽的淮揚菜;而油水多、重量大、煙火氣重、菜飯合一、缺乏擺盤變化的炒飯,自但是然地被貼上了市井江湖的標簽,與文人審美中細致的飲食發生了隔閡,也與揚州俗氣俊逸的城市抽象發生了反差。
從此當前,掌握言論力氣的士大夫們,在詩詞文章中,再也不會詠贊“碎金飯”之美味。
這是明天炒飯仍然游離于揚州主流飲食之外的,最基本緣由:并不是揚州人不吃、不愛吃炒飯,而是以文人文明為標榜的城市氣質,刻意疏忽弱化了炒飯的存在。

中國炒飯降服世界
失之東隅,收之桑榆。
唐宋之后,雖然中國精英階級的飲食審美逐步丟棄了炒飯。但這種偉大的食物,卻以另一種方式取得重生。
在閩南、在廣東,在中國北方最具陸地性的地域,隨著明清封關禁海政策的推行,本來被破碎丘陵地形阻隔的北方,得到了與中原王朝親密聯絡的紐帶。
一種特殊的文明不同步,在嶺南地域悄然醞釀。包羅潮州生腌、漳州生燙、泉州醋肉、莆田鹵面在內的眾多食品,都如工夫膠囊一樣,保管了許多唐宋以前的古韻古風。
炒飯也是。
當其他地域飲食中炒飯位置相持不下的時分,嶺南人卻越來越多地嘗試提升炒飯江湖的味覺天花板。北方特產的咸魚、雞粒、鳳梨、大蝦、火腿、叉燒、瑤柱……萬物都可入炒飯。
在福建廣東,無論正餐、點心,還是夜宵桌上,都能見炒飯身影。在茶餐廳里,總能聽到食客說換“炒底”,就是把白米飯換成炒飯的意思。
最值得一提的是,近代炒飯盛行的地域,恰恰是最早吹來西學東漸之風、最早大規模出海探究世界的地域。作為一種景象級飲食,炒飯被華人華裔們帶到了亞洲、歐洲、非洲、乃至美洲。

△圖片來源:pexels
中國炒飯,降服世界。
明天,英語世界里的“fried rice”,當沒有特指的時分,都會被加上前綴“Chinese”,這反映了炒飯這種食物與中國深入的關聯,更記載了百萬僑民下南洋的歷史、描畫了華人飄洋過海討生活的畫卷。
西北亞和南亞是最早承受中國炒飯的地域。外地濕潤、悶熱的氣候條件特別合適秈米的種植。和中國腹地盛行的粳米比擬,秈米顆粒長、脆度大、蛋白質含量高,煮熟之后顆粒清楚,充溢嚼勁。泰國人把它稱為“茉莉花香米”,印度人則稱之為“野米”。獨自吃口感不好,但特別合適烹成干身、油潤、脆口的炒飯。
從食材來說,炒飯在西北亞和南亞的盛行,有了立身之本。
越南炒飯與中式炒飯的類似度是最高的,雞蛋、米飯、小蔥與鹽的組合,勾勒出它的華夏筋骨。但香茅草、叉燒肉和煙肉的參與,則反映出西北亞的區域特征、遭到粵文明影響的習俗傳統和法殖民的歷史印記。
泰國炒飯的配料豐厚,來自陸地的扇貝柱、大蝦仁,伙同來自海洋的豬肉松、雞脯肉、鳳梨丁和蘆筍丁,最初一把堅果仁升華味道,彰顯了寒帶半島國度的豐厚物產。
印度炒飯少不了咖喱,但與醬汁撈飯不同,炒飯為了堅持干爽的口感,是不克不及用咖喱醬的,最地道的做法是用咖喱粉,再不濟瓶裝的油咖喱也行。這種食俗,反向影響了馬來西亞、印尼等國度。
緬甸炒飯會用到一種叫做Ngapi的食材,字面意思是“壓魚”。是一種由魚或蝦制成的辛辣糊狀物,發酵、腌制、研磨,曬干,參加新穎的黃瓜條,混合切碎的洋蔥、青辣椒和醋炒飯。
日式蛋包飯,本質上是自創了法國歐姆蛋(Omelette)的做法,在煎蛋里參加中式炒飯而成的“混血兒”。由于飯和蛋是分開處置的,炒與煎發生了不同風味,最初組合起來,再由番茄醬擔任其中的諧和者,成就了至今大受歡送的景象級食品。
實質下去說,蛋包飯就是明治維新西學東漸的時代,基于中國炒飯降生的日本改進料理。
此外,包羅菲律賓、柬埔寨、韓國、日本等國度,都降生出外鄉風情的炒飯。雖然調料配菜有別,但根本的烹飪邏輯,本質上都來自隔夜米飯、雞蛋、小蔥、植物油作為根底的中式炒飯。
一種典型的文明圈飲食風俗溢呈現象。

揚州炒飯,其實是揚州蛋炒飯
19世紀中葉開端,隨著鴉片和平的迸發,以及稍晚的淘金熱、拉美大開發。少量來自中國福建、廣東的移民涌入美洲,把炒飯帶到了世界上間隔中國最悠遠的中央。
對尊人重土、猛攻祖業的中國人來說,阿誰年代情愿出海當勞工的的人群,往往是來自最底層的、得到土地的赤貧階級。
他們沒有參鮑翅肚的念想,也沒有刀魚美蟹的偏好,一碗油水十足,咀嚼感到位,還分發著雞蛋和蔥花香氣的炒飯,就是一天勞作后莫大的恩賜。
市井江湖,方顯味道本性。
美國盛行的美式炒飯(American Fried Rice),其實質就是泰國炒飯。美國人會在泰式炒飯的根底上,參加切碎的熱狗腸和油煎面包塊,這是美國快餐文明對炒飯的另一種詮釋。它與西班牙燴飯改進而來的“什錦飯”(jamabalaya),共同組成了美國人對稻米的最根本看法。
美式炒飯源自美國西部淘金熱,但它最終的泰國化,則是二戰后泰國日益成為國際旅游目的地后,泰式飲食融合影響的后果。聰明的華人餐廳廚師,在原本油潤松化的炒飯上搭載了香茅、檸檬帶來的酸香氣味,使之更具張力、更投合美國人酸甜口的偏好。
與之相似的還有秘魯炒飯,它可謂明天秘魯的“國度特征”——簡直一切秘魯家庭都配置有一口圓底炒鍋,只為了可以隨時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炒飯。
在秘魯,炒飯被直接音譯成(Chaufa)。在與本地食材混合炒制后,炒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西班牙語后綴:比方雞肉炒飯叫Chaufa de Pollo,豬肉炒飯叫Chaufa de Chancho,海鮮炒飯叫Chaufa de Marisco。
假如說茶葉的出海、飲茶文明的興盛,代表了中國對世界影響的文雅、端莊、形而上的那一局部,那么炒飯在整個東亞、南亞地域的盛行,則出現了中國文明煙火氣味的另一種魅力。
或許是由于身在大洋此岸的華裔們心胸故國,又或許是劇烈的餐飲競爭誘發了品牌認識的萌芽,晚期華人開設的中國餐廳,都喜歡以中國元素作為店鋪和菜式招牌招徠生意。比方左宗棠雞、李鴻章雜碎等等。
天津飯,最值得一提。
這種20世紀初呈現在日本東京淺草西餐館的料理,做法是在攪勻的雞蛋液中參加蟹肉蟹黃、蔥花等,炒熟后整塊蓋在米飯上,再澆個芡汁。日本東部次要用番茄醬勾芡,口味近似蛋包飯,日本西部則用醬油和鹽勾芡,更像中國人愛吃的醬油炒飯。
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食物與天津的關系,它油膩的口味和復雜的調味,更與傳統津門菜式的作風大相徑庭。看起來,倒更像是由于天津作為開埠港口而被海內熟知后,在日本的閩廣廚師們為投合日自己口味而創造出來的食品。
以叉燒、雞粒、火腿、蝦仁和甜豆作為配菜的揚州炒飯,或許也是如此。

△圖片來源:pexels
“揚州炒飯”第一次見諸于揚州的文字,曾經是1982年。揚州商業技工學校戴立芝先生參與編制的《揚州教學菜點選編》中收錄了揚州蛋炒飯的制造辦法。
在1983年4月出版的中國小吃上海風味里收錄了揚州炒飯,以為是在上海的揚州飯店里制造的。
是的,上世紀80年代揚州的炒飯,還聲名不顯,事先不叫揚州炒飯,叫揚州蛋炒飯。這個接地氣的名字,和明天揚州街頭小館子的招牌一樣。
而在同時代的廣州,“揚州炒飯”曾經登堂入室,是廣州酒家、白晝鵝精致菜單上的座上賓。
很顯然,這不止是一種信息的落差,更是一種文明的傳達和再造。
到2002年,揚州本地的行業協會,曾經制定出了揚州炒飯的中央制造規范。受不受公認是一說,但它無疑在客不雅上促動了炒飯在揚州本地受注重的復興。
從此當前,淮揚菜精致的刀工和充溢古典氣味的文人審美,開端使用于炒飯這種貧民小吃里。美麗的蝦球、蓬煊的蛋松、翠綠不變色的青豌豆,都參與到了炒飯的制造中:它是構成最早的淮揚菜、成型最晚的淮揚菜。是淮揚菜體系中最熟習的生疏人。
兜兜轉轉繞著地球一周的炒飯,回家了。
羅伊·馬丁納說,只要在我們不需求外來的贊許時,才會變得自在。
技術有上下、藝術有流派,但食材的上下貴賤,說究竟,都是基于消費力程度和社會言論的成見罷了。
直面味道的自身,才干享用更好的味道。炒飯如此,世界如此。